2020-10-16
.jpg)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副教授
她专注于运用数据技术探索文化性、社会性数据中所隐藏的抽象关系,以视觉艺术表现而实现⽣动的信息传播。主要学术领域集中于:动态媒体设计、数字视觉化设计。她曾经在中国、日本及美国接受设计教育,于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担任⼈工智能访问教授、⽇本多摩美术⼤学担任研究员。向帆最近发表的作品《中国古代家谱视觉化》通过将历史人物数据可视化,构建了包含上千人的家族树,让人们可以“一眼千年” 宏观的历史景象,这个以视觉设计介入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获得2020年度国际数字艺术顶级会议SIGGRAPH优秀艺术论文奖, 发表于麻省理工出版社的科技艺术代表性刊物《莱昂纳多》;她的另一个作品《全国美展获奖油画作品视觉化》激起了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们对于当代中国艺术评价机制的反思。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视觉化设计、设计批评及设计史相关论文。
获奖经历:
2020 学术论文获得国际计算机图形顶级会议SIggraph2020 最佳艺术论文奖
2019 作品入选意大利⽶兰三年展中国馆
2018 作品入选法国《1,2,3 Data》数据设计展览 (2018)
2018 作品入选国际可视化会议( IEEE VISAP)视觉化艺术展(2018)
2012,2019 入选中国国家设计⼤展
.png)
SGDA:
您是如何接触到动态媒体设计、数字视觉化设计这一个领域的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领域深入研究呢?有什么特别的契机或者兴趣点所在吗?
✸ 向帆:
我没有选择动态媒体。2007年的时候美国设计师Donald Tarallo到广州美术学院来做讲座,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接下来学点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MASSART” 这句话我就记住了,虽然我也不知道MASSART是什么,但是直觉这个答案特别靠谱、简单和明确。
在线科普:
MASSART,麻省艺术与设计学院,建立于1837年,最初名为麻省艺术学校(Massachusetts Normal Art School)。学院由“新英格兰学校与学院委员会”及“国家艺术设计学院委员会”进行认证。学院的纯美术类课程很早就开始创办,近年来科技艺术类的课程也正在蓬勃发展。
SGDA:
✸ 向帆:
人有时候真的要依赖别人的大脑,就好像我们需要把文件要存在硬盘、云端一样,因为个人的视野、经历和认知能力都是有限定的。我很庆幸Don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建议,因为他在美国教书,那么肯定比我更清楚美国的设计教育目前需要什么,什么是热点。他甚至不需要给我清晰的逻辑推论、或者详细的说明,现在看来那是一个模糊经验所总结出的明确结果吧?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建议,有些建议我们是不愿意采纳的,是否采纳还是取决于当时自我的状态,以及对别人的信赖程度。
SGDA:
而您接受了这个建议,是否意味着,对过往的专业领域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看到了它的局限?
✸ 向帆:
每个人都会有厌倦期的。坦白说我至今没有看到中国在环境图形、导向标识的研究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仅仅就导向标识来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量增,导向牌无所不在,但是导向设计的创作集中在形式的变化(怎么变得更酷炫一点),但是内核(视觉信息的认知和形态的关系)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上个星期,中国美术学院的袁由敏老师问我,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在公共图形符号设计方面有所表现,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提问,可能在满街都是导向标示牌之后才是深入研究的时机吧?毕竟我们国家要走过从无到有、从有到漂亮,然后漂亮到有道理的几个阶段。
SGDA:
✸ 向帆:
在日本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偏向设计方法、设计工学、公共图形,重视理性和逻辑,但是我的老师太田幸夫先生他早年是学日本画的,茶道、花道、香道都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事情,他年轻时候又留学意大利,生活风格又有意大利的那种率性的作派。因此我留日的生活很杂糅;在美国最大的变化就是认识到当代艺术的力量,承认混沌、模糊、负面情绪的合理性,整个人就比较松弛了。影响我至深的老师Jan Kabu,虽然创建了动态媒体专业,实际上他出自平面设计的重要国家波兰,他对图形细腻的挑剔、优雅之中带着忧伤的家庭背景,所以在美国的专业学习,也是杂糅的。总得来说,我也不清楚是大蒜、酱油还是辣椒影响了我,经历就是一份火锅的蘸料。
.png)
▲2000年新年,从东京前往本州东部的盛冈过新年
.png)
▲2010年,在美国波士顿麻省艺术学院读书期间
SGDA:
✸ 向帆:
影响是肯定的。我父亲曾经是《科幻世界》的美术编辑,我从小生活在编辑部,跟着他看展览、去印刷厂、去出版社。他比较习惯否定我,所以我也就习惯否定他。虽然我大学学了视觉传达设计,但是我一直非常拒绝所有跟出版有关系的工作。父女关系,当事人自己其实很难定义的。
在线科普: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前身是《科学文艺》和《奇谈》,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曾承办过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是中国科幻期刊中一面历久弥新的金牌。
.jpg)
▲向帆幼时与母亲、父亲合照
SGDA:
✸ 向帆:
我不知道呢,我也不想要这个伏笔,那一代科幻作家和编辑的孩子们,按理说都 被”埋了伏笔“,但是没有人去做科幻。科技与艺术这个命题,又回来,很异样的感觉,迫使我反思现实,好像撞见了历史。
.jpg)
▲四川日报头版,80年代,被拔苗助长学英语。(聊天时提到“被拔苗助长的人生现在才能解码”)
SGDA:
✸ 向帆:
我觉得我爸爸都是见不得看到我“闲着”、“开心着”,他自己也不闲着,所以我成长在一个全家时时刻刻在学习的状态,至今我的论文量没有超过我妈,出版量没有超过我父亲。至今我还是在写论文、基本没有敢“闲着”“,骨子里没有叛逆哈。
关于我父亲的字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方正出版我父亲的钢板字几年了,他都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是因为“钢板字“对他来说是一个信手拈来的字体,那是他们曾经经历的日常,而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人会写这种字体了。作为一个设计的研究者,我认为”钢板字“这种风格的字体是有历史意义的,所以我给我爸爸布置作业,他写得很迷惑、很辛苦、很被动。字体写好之后,仇寅老师认为可以成为手迹系列的一个部分,仇寅老师把他们生成的字体发送给我试用。当我在电脑上敲出爸爸的字体的时候,顿时泪流满面,这种体验太特别了!我们每个人都肯定熟悉父母的笔记, 可是能够在电脑上敲出爸爸的字迹,是多么具有冲击力的心理体验;我曾经认为爸爸写下的每单个字是有瑕疵的,但是仇寅老师说手写字并不需要像通用字体那么平衡、精致,反而能保有手写字体本身的味道,这种角度的思考很具有启发性。再扩展一点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地域局限性,如何把局限性转换为一种强烈的特征、做出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每个人的独立命题。
.jpg)
.jpg)
▲方正向际纯钢板字
—
.png)
SGDA:
✸ 向帆:
SGDA:
在一篇文章下面我们看到您的朋友给您的评价说您是个喜欢把一堆东西摆在一起的人,对你来说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堆砌资料、视觉化数据的原始动力是什么呢?
✸ 向帆:
SGDA:
您的数据研究方向都非常特别,在确定选题之前,您都会考虑什么呢?
✸ 向帆:
全球有很多人在做着类似的工作,我只是在国内、在设计界稍微做过一些时间的人。选题的时候……, 我没有“选题”的意识,并不是很多题目给我选,我只是做我很想做的实验,就是一种创作的冲动。但是这种方法好像在体制内不太有用,我回国之后才知道很多研究者其实先要写“课题申请”,然后在很小的概率下求得资金,如果幸运地话再去做研究,没有拿到钱就不再做了。所以,我现在选择一个研究方向之前,考虑的事情就不那么单纯了,脑子越来越不太够用了, “选题”的意识会不会终止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呢?我也申报过“选题”,我不知道如何申报说明自己艺术创作的计划,因为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很多意外,我特别珍视“意外”的价值,有计划的时间就是执行,而不是等待许可,让其他人来决定这件事是否值得做下去。
SGDA:
✸ 向帆:
数字艺术最好玩的事情就是,人不能控制画面的一切,视觉成果的生成决定于随机和控制之间。我不太愿意看到100%被作者控制的画面,所以我特别不爱看电影,虽然周围的朋友都鄙视我这一点。
.gif)
.jpg)
.jpg)
.gif)
.jpg)
https://www.zeelab.xyz/A-Palette-of-CCTV-s-Chinese-New-Year-Gala- 1
SGDA:
您曾经和叶永烈、童恩正,还有高士其等前辈聊过的话题:“’艺术与技术的春天’就是现在”,那时候的你们都在讨论哪些内容?如今的时代您对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 向帆:
SGDA:
✸ 向帆:
一个作品一旦公开,社会的反馈就会超出想象。大众的关注度其实是寻求不到的,我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举例了一个运用流图进行新闻分析的案例,这个研究发现大部分话题都是主流媒体发起的,个人社交媒体主要是跟进的角色,从个人媒体逆袭到主流媒体的案例凤毛菱角,因此个人对博取大众关注度的努力其实都是白费力气。
.png)
.jpg)
https://www.zeelab.xyz/Taichi-Motion
▲太极信息视觉化设计
✸ 向帆:
http://zeelab.cn/AP/desktopNew.html
设计师不是一直在做大量信息的解码和转码工作嘛?解读需求和问题,转化成为设计方案。
SGDA:
就您现有作品而言,“视觉”本身已经不是最核心的支撑部分,这是否意味着,您本身已经不算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设计师”或“设计师”?如果不是,能为您自己的身份下一个更准确的定义吗?
这个提问是包含一个判断之后再提起问题的。首先,这个判断蛮有趣的,我所做的作品中,视觉设计的工作是核心的位置,无论是在数字人文领域、计算机图形领域,艺术设计展览我的作品都是被理解为设计作品和艺术作品的而入选的。只是不是目前大家所熟悉的语境吧?如果不是视觉设计领域的话,那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视觉设计领域到底包含什么?它的内核是什么?同时,对比一下非视觉设计领域的成果,你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提问反而透露出我们对“视觉设计“的理解有不同的理解吧,也就是我国目前阶段的文化语境问题。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设计师“是什么呢?是指包装设计、品牌标志设计、书籍设计吗?其实我最近也完成过包装设计和书籍设计的工作,甚至正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书,好像大部分视觉设计师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传统行业吧?很多好的书籍设计师还是在创作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他们不会说自己是传统设计。非要说传统的话,我也是在传承各个年代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即便是局限在数字艺术领域的话,那最早的数字艺术是出现在1960年代的。
就“身份”而言,我的社会身份就是教师,而且是美术学院视觉设计传达的教师,你看我是不是一个甚至在传统设计语境下最不会有身份问题的人?这个问题逻辑没有理顺,但是内涵我可以理解。答案是这样的:“视觉设计师”的身份问题显现了我们如何定义视觉设计的研究范畴,原来的领域可能不够用了。我也不在乎是个视觉设计师,还是XX设计师,不能界定的身份恰好会赋予创作的自由。”身份是一个陷阱”,这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Laurie Anderson说过的,她认为这是策展人给艺术家的陷阱。
.jpg)
▲向帆和朱舜山先生为主导的论文于2020年8月获得了国际顶级学术会议SIGGRAPH年度最佳艺术论文奖
—
.png)
SGDA:
没有。但是有助于理解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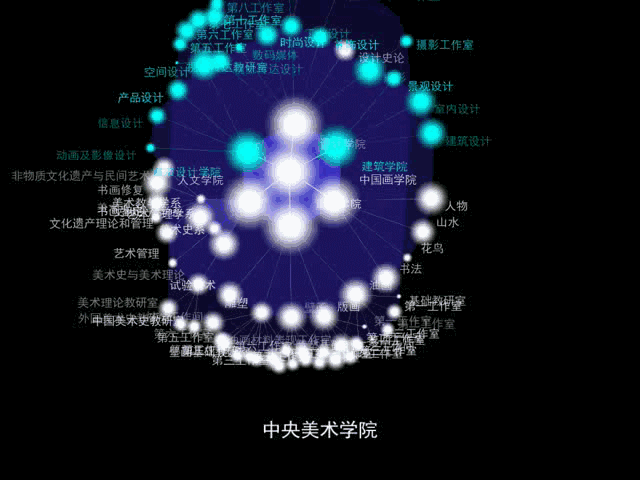
https://www.zeelab.xyz/The-Structural-Formula-of-Design-Colleges
✸ 向帆:

SGDA:
✸ 向帆:
渴望学习别的技能,比如种花呀、做饭呀。
.jp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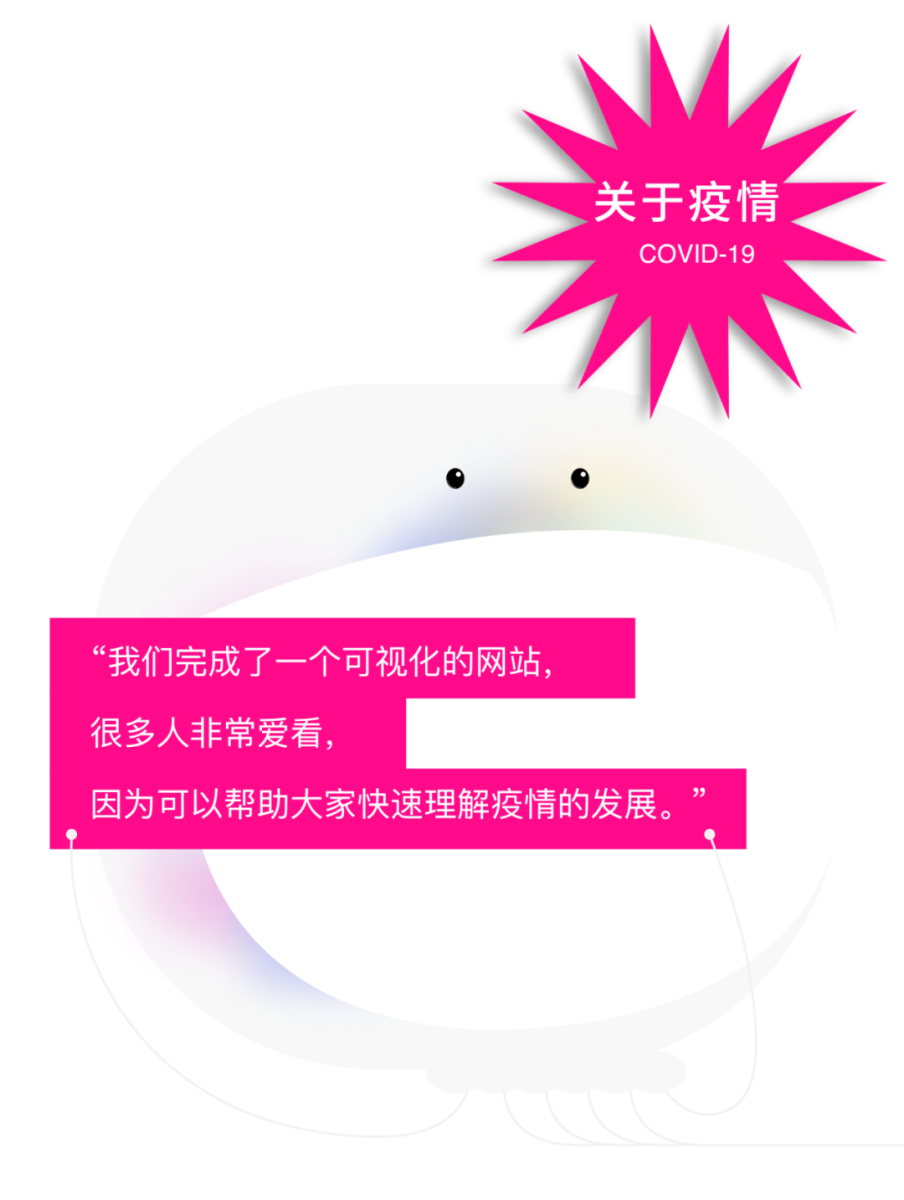
疫情对您的生活、研究有什么影响吗?您做出了什么样的应对举措呢?疫情期间是如何提升自我价值的?
答不上来。我们首先面对如何上网课的问题,一个人对着几十个不露脸的同学讲课,宛如在黑暗中的呢喃,这种教学现状首先需要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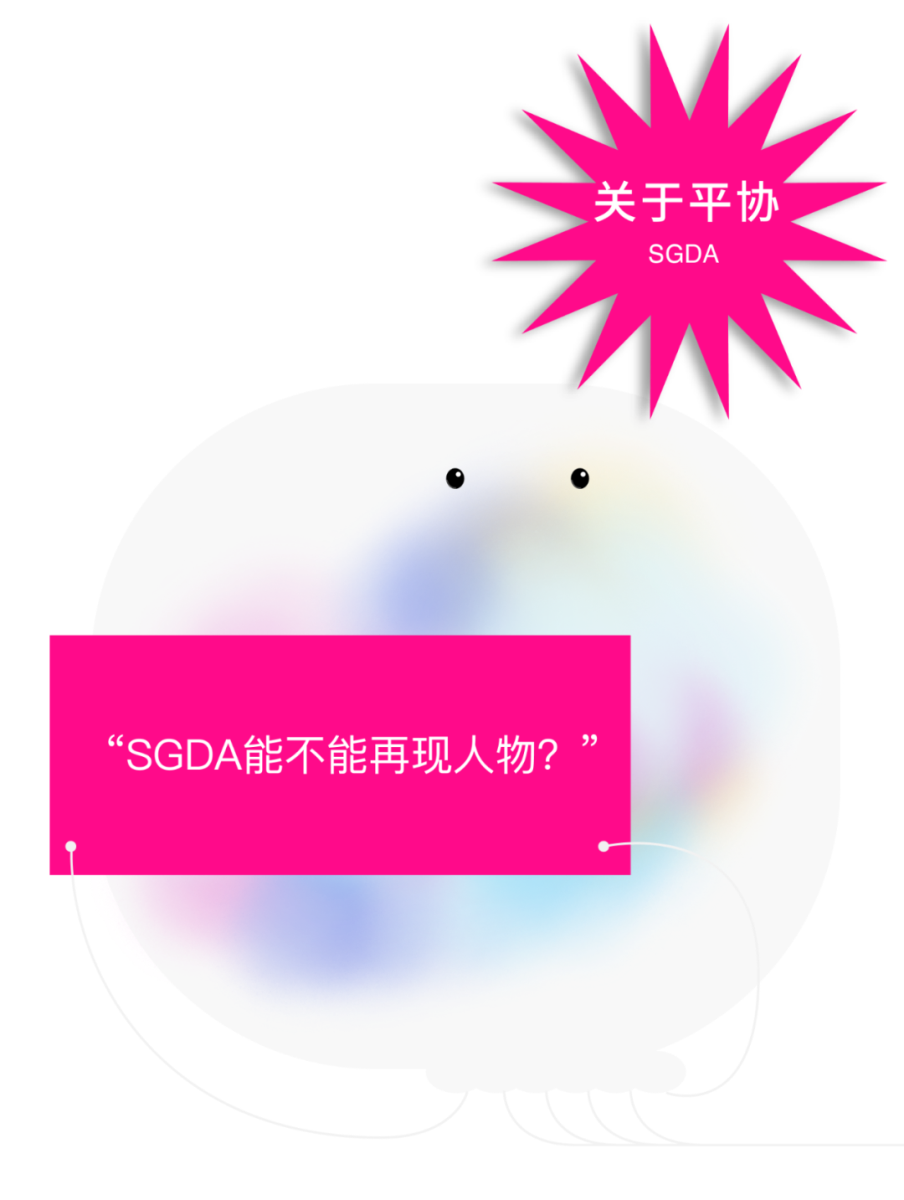
SGDA:
您最初是怎样接触到SGDA?是否有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1994年的时候,好像是平协第二次年会,在华强北。大家会各自带礼物去参加活动,然后抽奖交换。我记得我抽到了一管牙膏,印象深刻。
.jpg)
.jpg)
▲2013GDC在香港,与王粤飞老师与陈绍华老师
王粤飞老师的推荐信:我想我找到一位女性设计师朋友,推荐给大家,她是来自淸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向帆老师,己多年从事设计教学与实践。她喜欢追随真理,对摇唇如簧生厌,她喜欢设置批判性项目展开,以示后人,正如她天生不屑审美低下的作品,和我一样嫉恶如仇。她是原创设计的捍卫者、国际间交流的先锋。我想,她正是我们协会需要的一员。
王粤飞
2019年10月
对于SGDA的未来发展,您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有什么期盼与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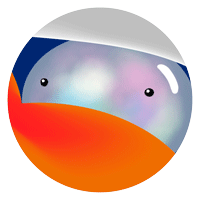
我们将随机抽取回答正确的小伙伴送出神秘礼品一份!
.jpg)
品牌创意/版权保护平台,于2005年7月创立,以探讨专业品牌创意为基础内容,致力于打造中国最知名的版权保护专业品牌创意网站。9号旗下还有总标头(知识产权平台)及掘物(创意电商平台)等。
官网 Web|www.gtn9.com
SGDA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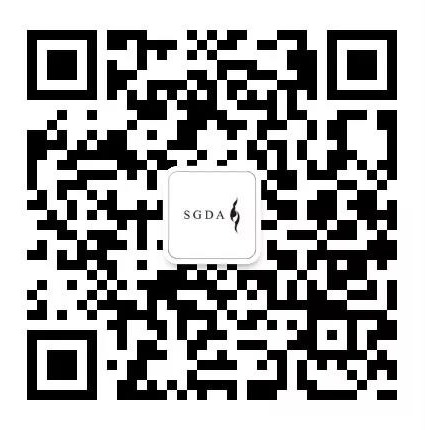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合作意向,请给我们写邮件吧:)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zl2hQ0m1Ud7nPjJ4hI_rw